你知道19000萬年的“恐龍之城”聚集在我國重慶嗎?
日前,重慶自然博物館新館恐龍展廳在閉館升級后重新對外開放,升級后的展廳呈現了更多“重慶元素”——“上游永川龍”“神州巴渝龍”等近10件重慶恐龍化石標本悉數亮相。短短幾天,上萬市民前往參觀,在重慶掀起了一股“恐龍熱”。

添加微信好友, 獲取更多信息
復制微信號
重慶恐龍家族都有哪些重量級恐龍?上億年前,為何會有這么多恐龍棲息重慶?近日,記者前往重慶自然博物館,查訪重慶恐龍檔案,揭開重慶遠古恐龍世界的奧秘。
重慶恐龍曾是世界級“明星”
走進自然博物館特展廳,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件巨型蜥腳類恐龍化石標本,它嘴部微張、昂首挺立,似仰天長嘯,看上去氣勢十足。
“這是有‘東方巨龍’之稱的合川馬門溪龍,是迄今亞洲更大、保存最完整的巨型恐龍,被譽為‘中國恐龍的明星’。”重慶自然博物館館長歐陽輝介紹說,合川馬門溪龍也是目前世界上已發現的脖頸最長的恐龍,其體長約24米,脖子長度幾乎占到體長的一半。阿聯酋國家博物館曾出價3000萬美金,想把它收入囊中,充當鎮館之寶。
上世紀70年代前,中國肉食恐龍化石僅發現過零星牙齒、少量破碎骨骼。為此,國外曾有人稱:“在遙遠的侏羅紀,中國只有素食龍,這是造成中國人性格軟弱、逆來順受的原因。”
然而,1972年至1977年,在重慶永川相繼發現巨型肉食龍化石,推翻了這一謬論。當時這一發現在國內外引起了轟動,還吸引了英國大英博物館的古生物專家專程前來參觀。至此,中國肉食恐龍終于得到世界認同。
重慶主城是恐龍化石密集分布的地區
在重慶,究竟有多少這樣珍貴的恐龍化石?今年,在完成全國之一次可移動文物普查任務的過程中,自然博物館對重慶本土發現的恐龍化石進行了全面清點。“恐龍主要有蜥腳類、獸腳類、鳥腳類、劍龍四大類,而這些恐龍化石在重慶都曾有發現。”歐陽輝說,截至目前,全市共發現恐龍化石點40余處,出土較完整的化石近10具。
更神奇的是,重慶主城竟是恐龍化石密集分布的地區。渝中區朝天門、南岸區銅元局、江北區大石壩、九龍坡區馬王場、北碚區金剛碑、澄江鎮、童家溪鎮等地都曾發現過恐龍化石。其中,北碚區是發現恐龍化石較多的地方,共發現13處。
究竟是什么原因,引得這么多恐龍棲息重慶?“重慶可以說是一座‘恐龍之城’。”歐陽輝介紹說,1.35億年前的侏羅紀時代,那時的重慶遍布沼澤和湖泊,氣候炎熱潮濕,岸邊森林密布、灌木叢生,這些條件特別適合恐龍居住生活。
重慶自然博物館的發展歷史
重慶自然博物館的前身為1930年盧作孚先生創辦的“中國西部科學院”,以及1943年由十余家全國性學術機構聯合組建的“中國西部博物館”。
中國西部科學院是我國之一所民辦科學院,是盧作孚致力于國家現代化目標,將“科學救國”與“實業救國”思想相結合,積極探索救國、強國之路的光輝典范。以“從事于科學之探討,開發寶藏,富裕民生,輔助中國西部經濟文化事業之發展”為宗旨,在西部早期開發建設中扮演了“排頭兵”角色,為民國時期的經濟建設和科學文化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抗戰時期,國民 *** 西遷重慶,一大批重要的學術機關也向大后方遷移。中國西部科學院及其所在地北碚,接受了許多著名學術機構和一流的科技人才的轉移安置,一度成為中國科學界的“諾亞方舟”和“戰時學術研究中心”。
1943年,中國西部科學院聯絡內遷北碚的中央研究院動、植物研究所等十余家科研機構又在文星灣創建了中國西部博物館。盧作孚借讓中國西部科學院“惠宇”大樓作為博物館的陳列主樓,辦公室、實驗室、圖書室等則在“惠宇”附近另行建筑。以“從事科學教育之推廣及專門學科之研究”為宗旨的中國西部博物館,設地理、地質、工礦、生物、農林、醫藥衛生6個分館,是中國人自己建立的、綜合了最多學科的之一家自然科學博物館。
1950年,中國西部科學院和中國西部博物館由西南文教部接管。
1952年,重慶自然博物館改為西南人民科學館。
1953年,重慶自然博物館并入西南博物院,更名為西南博物院自然博物館。
1955年,西南博物院改組為重慶市博物館。
1981年,四川省人民 *** 在重慶市博物館增掛 “四川省重慶自然博物館”牌子。
1991年,重慶自然博物館獨立建制。
中國西部科學院疊溪地震調查及其著述《四川疊溪地震調查記》
歐陽輝 侯江 張鋒
(重慶自然博物館)
1933年8月25日下午重慶自然博物館歐陽輝職稱,四川茂縣松潘等地發生強烈地震。15時50分30秒重慶自然博物館歐陽輝職稱,地震中心在北緯30°、東經103.7°的疊溪的震級為7.5級。國內重慶自然博物館歐陽輝職稱,北京鷲峰、南京地震臺幾乎同時記錄到震波。國外,馬尼拉、大阪、棉蘭、孟買、哥本哈根、漢堡、檀香山、巴黎、突尼斯、悉尼、多倫多、威林頓、渥太華、拉巴斯等世界百多家地震臺都測收到重慶自然博物館歐陽輝職稱了這次震波。
此次地震發生之時,巖石飛崩,擊死居民,村舍沉沒,岷江上游因之隔斷,余波續震四五日不絕,疊溪一帶,正當地震中心,罹禍尤為慘重,地震造成6945人死亡,傷1萬人以上,疊溪全鎮陷沒,岷江江水被山體崩塌物堵塞斷流,形成中國地震史上較為突出的地震堰塞湖,其壩高有的甚至高達百余米。之后決口造成的次生洪災又奪走數千人生命,震區傷亡慘重,共計死亡人數近萬人。自1900~1950年,據不完全統計,中國7級以上地震59次。[1]這是民國時期四川更大的地震,也是民國時期中國最強烈的地震之一。
一、關于1933年疊溪地震的調查
地震為人類最為慘烈的災害,疊溪地震發生后,地方 *** 及中央相關部門派人深入災區進行調查。
震后近1個月后,四川善后督辦劉湘派成都水利知事公署技術主任全晴川率四川大學學生諸有彬等10余人前往調查,重點是岷江地震堰塞湖的積水情況,調查時間9月至10月9日。12月7日善后督辦劉湘再派即任的成都水利知事周郁如同督署上校參謀郭雨中帶30余人再次調查,歷時5天,提出了疏導疊溪地震堰塞湖的具體工程方案。[2]
學術機構的調查有受北平地質調查所委托的中國西部科學院地質研究所,另外還有四川大學等。
四川大學的疊溪震區野外考察,由該校生物系(開設了地質學與古生物學課程)師生組成12人地質考察團,教師周曉和帶隊,于1933年12月21日出發,次年1月14日回到成都,歷時25天。考察以了解灌縣至疊溪一帶的地質、地史、古生物和疊溪地震的震災情況為主。
另外,以個人身份進行考察的有地理學家徐近之。1933年秋,徐近之在青海地區考察,聞疊溪地震消息,立即于10月21日至11月29日,對疊溪震區乃至整個岷江上游進行歷時40天的實地考察。[3]
中國西部科學院的疊溪地震考察。為研究此次松茂地震來源狀況及原因等,1933年10月,該院地質研究所主任常隆慶(北京大學地質系畢業后即在北平實業部地質調查所工作,1932年9月由所長翁文灝推薦,受盧作孚邀請到重慶北碚中國西部科學院任地質研究所主任)、羅西伊(即羅正遠,字君平)奉實業部地質調查所之命,前往疊溪實地調查松茂地震,所有一切費用概由北平地質調查所負擔。考察歷時兩個月。
由于地震區域遼闊,人力有限,在實地考察中輔以信函調查。由中國西部科學院致函各縣 *** 及文化機關,請其告以當地情況,同時又發出通啟,致各界人士公啟、致各報館函,征求各地關心科學之人士予以援助,賜以資料。調查過程中,擬就表格一張,油印分寄川中各縣教育局、建設局以及中級以上學校,發出地震調查表,以便調查參考和將來繪制地震區域強度圖。[4]
地震強度調查表[5]
(此表共分十度,請將所在地的地震強度與此表相當之度數注明,寄回巴縣北碚場中國西部科學院地質研究所為禱)
一、人不能覺。
二、甚少數 *** 者覺之,樓上較易。
三、少數人覺之,不恐慌,經重慶自然博物館歐陽輝職稱他處報告始確信地震。
四、屋內覺者多數,屋外少數,器物微動,地板或響懸物稍動。
五、屋內人皆覺之,屋外人多覺之,睡者驚醒,少數人驚逸,搖鈴鳴,時鐘停,懸物搖。
六、人人皆覺恐慌,爭出,器物墜落,不堅固之房舍稍有損傷。
七、鐘鳴,煙囪倒,屋瓦落,多數房屋稍有損傷。
八、少數房屋毀壞,多數重損,少數人受傷,無死者。
九、少數房屋全毀,多數重損,不能復居,人煙稠密之處,死人頗多。
十、多數房屋毀壞,人口多數死亡,地裂山崩。
附注:
甲、地震發生于民國 年 月 日午 時 分
乙、震時間共
丙、以后又震動若干次,在何月何日何時發生震力相當上表何度。
填表機關
填表人
民國 年 月 日寄
調查途中,常隆慶給地質調查所所長翁文灝致函報告地震現場考察情況,翁文灝附記數言。1934年,常隆慶基于收集、拍攝的大量地震資料,對調查情況進行分析,寫成《四川疊溪地震調查記》。在近代,由于戰爭、交通、經費等原因,對地震的調查也有采取函調的方式,給所在地區及相關單位發函收集資料,再分析匯編成冊。而現場的科學考察就顯得尤為可貴和難得了,能夠在之一時間掌握之一手資料。采用現代科學 *** 對大震現場進行科學考察,在我國西南地區還是之一次,在國內也僅次于1920年寧夏海原大地震后的現場科學考察(震后次年,內務、教育、農商三部曾派翁文灝、謝家榮等六委員赴災區調查,這是我國地震史上之一次對大地震所作的詳細的科學調查)[6]。在中國近代地震地質調查研究中,中國西部科學院的疊溪地震調查是這一時期重要的實地地震調查活動。
二、關于1933年疊溪地震的研究著述
疊溪地震1933年8月25日發生后幾個月,翔實的地震報告就刊行出來。
中國西部科學院地質研究所常隆慶連續刊發幾篇調查記,有《疊溪地震調查記》,刊發于1934年5月的《中國西部科學院地質研究所叢刊》之一卷第三號;《四川疊溪地震區調查記》,刊發于《國立北平研究院院務匯報》1934年第5卷第1期上[7];《疊溪地震調查記略》,刊發于《新世界》1934年第38期。[8]
除此之外,徐近之的《西寧松潘間之草地旅行》和《岷江峽谷》刊發在《地理學報》1934年第1期(創刊號)上。(《岷江峽谷》中“地震后峽谷實察紀要”,對疊溪地震災害和水患作了真實的記述和分析,并提出震后建議對策:預防地震災害、疏導堰塞湖積水、建筑物抗震、交通及通信對策、保護岷江河谷生態環境、發展山區經濟等)[9];四川大學編著《疊溪地質調查特刊》1934年7月出版(國立四川大學秘書處出版課,1934年7月出版,54頁32開,有圖、表、照片)。內收調查報告6篇,調查地質情況,并有考察日記,疊溪地震損失統計表及羌人風俗等,其中最珍貴的資料是細致到村寨的地貌改變、房屋垮塌、人員傷亡的考察記錄[10];地質調查所李善邦著《四川疊溪地震記錄簡報》發表在《國立北平研究院院務匯報》1934年第5卷第3期[11](當時,世界地震學還處于相當初級的階段,沒有“震級”的概念和定義)。李善邦采用巧妙算法分析計算此次地震的發震時刻和震源深度,測定疊溪地震參數,所確定的震中坐標相當準確,與宏觀震中疊溪的位置非常相近,至今基本采用這一數值[12]。在常隆慶到四川地質調查所后,著《四川疊溪地震調查記》,刊發在《地質論評》1938年第3卷第3期上。
這之后二三十年,尤其到了20世紀70~80年代,關于四川疊溪地震的調查、記錄和報告又才陸續增多。有“疊溪地震瑣記和對地震的初步認識”(周郁如,1958年手稿)、“1933年四川疊溪地震補充調查報告”(國家地震局西南烈度隊,1973年11月打印稿。另一資料記為“疊溪地震補充調查報告”國家地震局西南烈度隊影響場組,1973,未出版)、“1933年疊溪地震宏觀調查表”(地震地質隊松潘大組,1977年8月手稿本)、“1933年疊溪地震調查報告”(成都地震大隊地震地質隊,1977年11月復寫稿。另一資料記為“1933年疊溪地震調查報告”四川省地震局地震地質隊,1977,未出版)、“四川省歷史地震資料匯編 1933年疊溪地震”(討論稿)(王元海,1977,未出版)、“疊溪1933年地震調查材料”(阿壩州地震史料小組,1978年5月復寫稿)、《四川地震資料匯編(之一卷)》(《四川地震資料匯編》編輯組,1980,四川人民出版社)[13]、《疊溪大地震親歷記》(張雪巖,《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七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疊溪7.5級地震的地質構造背景及其對發震構造條件的認識》(唐榮昌、蔣能強、劉盛利,《地震研究》1983年第6卷第3期)[14]、《1933年疊溪地震》(四川省地震局著,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83)[15]、《徐近之實察疊溪地震及對震后的建議對策》(江在雄,《山西地震》1994第3期)。
常隆慶所著一系列關于四川疊溪地震的調查報告,在后來的疊溪地震研究中一直起到重要的參考作用。1983年由四川省地震局編著的對疊溪震區現場考察、研究總結的著作《1933年疊溪地震》參考了常隆慶的著述,尤其對于分布在不同經緯度的各地點的地震烈度、場地條件、震害情況等提供了直接而翔實的參考,一些照片,如常隆慶1933年所拍攝的“較場東側臺面地震時被斷成階梯狀”被采用。[16]其著述被引用和參考還見于諸如《四川地震資料匯編(之一卷)》[17]、《中國巖石圈動力學概論〈中國巖石圈動力學地圖集〉說明書》[18]、《四川省巖石地層》[19]、《中國水利百科全書——水利工程勘測分冊》[20]、《中國典型災難性滑坡》[21]等。
而1934年常隆慶所寫的約2.6萬字的《四川疊溪地震調查記》,將疊溪地震情形及前后事實,旁征博引,附以照片、圖件和統計表格,對地震各災區,尤其以疊溪為中心的疊溪南路、西路、北路的具體情況,作了翔實的記錄。記述了疊溪震中區各村寨房屋建筑破壞、人畜傷亡、山崩地陷等地震破壞狀況,并對地震成因作了初步分析,說明當地地震地質特點。這是中國近代地震地質研究的重要著述,對疊溪及其周邊震區的崩塌滑坡、交通阻斷、人員傷亡、水災過程以及震中區的地質地貌特征、余震序列等情況的詳細敘述,成為我國以科學 *** 記載疊溪地震的之一篇詳細而確實的學術報告。
三、結語
中國是地震活動頻繁的國家,對于地震學的研究,近代中國學者從現代科學的角度多加著力, *** 也視為重要事業而加以注意。對于民國時期中國最強烈的地震之一、同時也是民國時期四川更大的地震——疊溪地震,中國西部科學院作為之一個專業學術機構進行調查,并寫下之一篇專門學術報告《四川疊溪地震調查記》。中國西部科學院的疊溪地震調查及其著述,其詳細的現場考察和研究,對地震前兆、震后效應、地震現象、地震后的破壞現象、社會影響,地震發生類型與序列特征等的描述,為當時和今后的疊溪地震研究。例如,區域地震研究、地震地質研究、歷史地震研究等多方面,提供可靠的科學數據和研究的可比性,是重要的科學考察和學術文獻。
參考文獻
[1]齊書勤.中國早期的地震科學考察[A].見:王渝生主編.第七屆國際中國科學史會議文集[C].鄭州:大象出版社,1999,405
[2]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茂汶羌族自治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茂汶羌族自治縣志[M].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7,38~39
[3][6]洪時中,徐吉廷.歷史將永遠銘記他們——記在疊溪大地震的考察、研究和救災工作中作出貢獻的幾位前輩[J].國際地震動態,2009,(2):34~35:30~31
[4][5][9]《嘉陵江日報》1933-11-18、1933-11-20~21、1933-11-5.見:龍海編輯.中國西部科學院調查疊溪大地震紀實[N].盧作孚研究.2008,(2):50~52
[7]陳尚平等.中國近代地震文獻編要(1900~1949)[M].北京:地震出版社,1995,316~318
[8]江蘇省地震局《中國地震科技文獻題錄大全》編纂組.中國地震科技文獻題錄大全[M].北京:地震出版社,1988,9,17
[10][11][12][15][17]《四川地震資料匯編》編輯組.四川地震資料匯編(之一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301~303,315~316,317~319,463~464,541
[13][16]四川省地震局.一九三三年疊溪地震[M].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83,69,圖版10
[14]《四川地震年鑒》編輯組.四川地震年鑒(1983)[M].成都:四川省地震局出版,1984,156
[18]《中國巖石圈動力學地圖集》編委會編,丁國瑜主編.中國巖石圈動力學概論《中國巖石圈動力學地圖集》說明書[M].北京:地震出版社,1991,565
[19]辜學達,劉嘯虎.四川省巖石地層[M].武漢:中國地質大學出版社,1997,372
[20]徐乾清,陳德基主編,門光永等撰稿.中國水利百科全書——水利工程勘測分冊[M].北京: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2004,70
[21]黃潤秋,許強.中國典型災難性滑坡[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93
上海自然博物館有恐龍嗎?
上海自然博物館5月25日晚開啟“恐龍季”重慶自然博物館歐陽輝職稱,活動將持續至7月底。
博物館之夜 鄭瑩瑩 攝
當晚重慶自然博物館歐陽輝職稱,作為“恐龍季”的首個主題活動,“博物館之夜”開啟,現場,觀眾聚集在館內生命長河展區巨大的阿根廷龍和埃及棘龍模型下,仿佛“置身”于原始而神秘的遠古時代。
活動伊始,上海科技館黨委副書記、上海自博館管委會主任姚強致辭;上海科技館理事長、上海科普教育發展基金會理事長左煥琛宣布,2018上海自然博物館恐龍季正式開幕。
160余名大小觀眾參與其中,活動共設置三個環節,之一個環節是恐龍脫口秀和現場繪畫,來自重慶自然博物館的歐陽輝館長和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徐星研究員為觀眾帶來科學脫口秀。同時,來自中國香港的古生物畫師張宗達根據生命長河展區的標本現場繪制一幅棘龍場景復原圖。
第二個環節是夜游博物館,自然博物館的研究人員、展覽和教育的策劃人員從幕后走到臺前,帶領觀眾走入夜晚的自然博物館,分享古生物背后的科學故事。
最后一個環節是工作坊,按照不同的活動內容分為四組:化石挖掘、化石拓模、恐龍魔力倉和恐龍大派對,現場觀眾在夜游中感受博物館的魅力。
在活動現場,主辦方還為觀眾帶來了自然博物館最新出版的青少年科學漫畫《恐龍不好玩》,該書通過270余幅妙趣橫生的原創漫畫,講述了六段驚險 *** 的旅程,讓讀者在追蹤一系列神秘案件的過程中,逐步揭開隱藏在恐龍家族背后的秘密。
據悉,上海自然博物館推出的“恐龍季”活動,以“來,一起尋找失落的世界”為口號,旨在倡導公眾保護生態環境,傳遞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活理念。活動對象主要為親子家庭、科學愛好者以及恐龍發燒友。
活動期間,將舉辦五大主題活動,包括博物館之夜、少年嘉年華、綠螺訓練營、科學家面對面以及綠螺講堂——恐龍總動員系列,同時還將恐龍作為線索,與自然博物館日常教育活動相結合,從周二到周日,每天都會開展恐龍主題活動,包括恐龍說說說、重慶自然博物館歐陽輝職稱我的恐龍我來畫、恐龍獵人訓練營、尋找精靈龍、遇見恐龍達人以及恐龍偵探等。另外,自然博物館的官方網站、微信公眾號也將推出線上活動,讓公眾了解古生物知識,感受自然科學的魅力。
中央地質調查所抗戰內遷北碚史實
歐陽輝 侯江 張鋒
(重慶自然博物館)
一、引言(歷史契機)
抗戰時期,中央地質調查所為避戰亂,向西撤遷。1937年11月從南京撤退,12月到長沙,1938年7月從長沙內遷重慶,1938年秋到渝,并在滇、桂兩省設辦事處,1939年春在北碚建成辦公樓,開始了戰時相對穩定的科學工作,調查礦產、土壤、古生物,傾注全力于西南資源的研究,成為戰時國內礦產資源調查研究中心。地質調查所能在紛亂的戰時安定下來,直接得益于中國西部科學院。在此,“中國之一個名副其實的科研機構”繼續研究工作,使地質學這門中國近代率先興起、成就更大的自然科學的科研血脈得以傳承,并與其他內遷北碚的科研單位一道,形成科學事業中心,共同構成戰時內地科學之大觀。
北碚位于重慶市北部,地處江北、巴縣、璧山、合川4縣(民國時期行政區劃)交界,水陸通達,交通便利,自然條件、地理條件優良。1937年7月,抗戰發生,北碚劃為遷建區,戰區機關相繼西遷,紛至沓來,遍及八鎮。有學校、研究機關、工廠和其他機關,以學校和學術機關尤為眾多。僅在中國西部科學院舊址惠宇及其附近地區,就有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等多家單位。
1937年11月中旬,國民 *** 命令各機關遷移。地質調查所倉促奉令,全部動員,于16~18日3天內,將圖書館、陳列館、各辦公室、化學試驗室及土壤室的重要物件,晝夜趕工裝箱,于18日將202個已裝箱件運赴南京下關。南京旋告緊急,代所長黃汲清組織地質調查所內遷武漢。長江航運吃緊,地質調查所緊急裝箱的202箱重要書刊積壓下關碼頭難以啟運。黃汲清求助于當時兼任行政院秘書長的翁文灝,翁文灝找到民生輪船公司總經理、中國西部科學院院長盧作孚商洽,使其迅速裝船,12月全部運抵長沙。1938年7月,武漢告急,地質調查所再次搬遷,先落腳在重慶市內,后因避免空襲,再度搬遷,最后落腳北碚,書刊、儀器暫時存放在中國西部科學院和其下屬機構兼善中學內。
地質調查所的內遷是奉1937年國民 *** 各機關遷移命令行事,而黃汲清選擇北碚,則完全出于盧作孚與其胞弟——北碚行政長官嘉陵江三峽鄉村建設實驗區區長盧子英的熱情邀請。“回憶兩年前各機關感先生及子英先生盛意,欣然遷來北碚,并蒙假惠宇房舍以辦公,復借予地皮使建新屋。”1940年5月18日黃汲清致盧作孚的信函中談及此事。
對于地質調查所,盧作孚早有所見識和佩服,并一直保持密切聯系。1930年為籌建中國西部科學院而進行的華東、華北以及東北的組團考察活動中,在參觀了地質調查所后他對丁文江說:“我們覺得南北走了一圈,難得看出極有成績的事業,地質調查所總算有成績了”。1931年1月2日中國西部科學院在兼善中學召開之一次籌備會議,就把中央研究院、靜生生物調查所、中國科學社、地質調查所、美國芝加哥博物院、瑞典博物院等學術研究機關列為其聯絡事業。
鑒于多年的交往與支持,地質調查所遷入之后盧作孚對他所敬重的地質調查所傾力相助,借出西部科學院辦公樓作地質調查所辦公場所,同時又在西部科學院院內借予地皮新建辦公大樓,1939年初速建辦公樓,同年春建成。磨片車間在靠江邊的一排平房內。圖書館則建在距北碚1km的魚塘灣。建筑新圖書館,是為圖書儀器安全起見,并因新建大廈(指辦公樓)不敷應用,特于北碚近郊青崗坡地方建一新樓,下層為圖書陳列及閱覽室,上層為土壤研究室及古生物研究室,1939年開建,1940年建成。1938年成立的昆明辦事處因滇越邊界時局日緊,1940年10月起取消并入北碚總所,重要標本、圖書、儀器和大部分工作人員遷碚,在天生橋租一小樓,為第三辦公室,計房屋六大間,樓上為新生代研究室和宿舍,樓下為化學試驗室。
關于遷址,在秦馨菱的回憶中是這樣敘述的:“1938年又遷往重慶復興觀巷與四川省地質調查所合署辦公。1939年春又從重慶城內遷往北碚在惠宇旁自建的新大樓內”。遷渝辦公時間是8月18日,詳細地址重慶小A子復興觀巷5號。
此時雖遠不及北京時期、南京時期那種良好的、國內一流的辦公環境,然而,從所設置的之一辦公處(惠宇)、第二辦公處(魚塘灣)和第三辦公處(天生橋)來看,在戰時的狀況下,還是達到了相當的規模,為科研工作的展開提供了硬件保障。
對于此次內遷,代所長尹贊勛在1941年12月14日地質調查所25周年紀念會上的工作近況報告中這樣提到:“黃汲清先生受命于抗戰之初,于艱苦之中,領導同人繼續工作,迄無間斷,又將大批圖書標本儀器材料,一再遷運,而達后方較為安全之地帶,厥功甚偉。”的確,因之地質調查所才得以在國難嚴重時期安身立命,不但老的機關還能維持,而且有不少新的機關相繼成立,20年來地質界的心血得以保存,科研工作的延續性得以保持,并繼續發揮其在地質科學上舉足輕重的作用。
二、調查科研合作 交往聯系密切
1.盧作孚對地質調查所的幫助
中國西部科學院院長盧作孚對于抗戰內遷北碚的地質調查所以及其他一些科研機構,給予了許多實際的幫助。除遷來之初的提供房舍安頓、提供地皮建房,到遷來后保證正常運轉的具體事項,可從1940年黃汲清與盧作孚的往來信函中略見一斑。
1940年5月18日黃汲清就大明染織廠停供惠宇各機關電力一事向盧作孚致函,懇請盧作孚勸告大明廠主持人繼續供電,設法維持惠宇各機關用電:
作孚先生大鑒:
在渝兩次趨謁,未獲晤面,至悵惘。
茲有一事欲為先生陳述者:爰北碚敝所辦公室及惠宇各機關所用電力,一向由大明染織廠供給,至為便利。乃自本月一日起,該廠即實行停止供電,所持理由為奉命增加生產,電力不足,該廠并囑惠宇各機關及敝所向北碚公共電廠接洽用電,以為補救之計。各機關聞訊之下,深同詫異,乃由工業試驗所顧所長毓瑔及清向該廠交涉,請其繼續供電。當與該廠主持人查、謝二君商討良久,卒不得要領。清等以北碚各種建設事業或由先生所提倡,或為先生所主持,而大明染織廠之組織亦由先生擔任董事長,故謹代表敝所及惠宇各機關呼吁于先生之前。
查惠宇各機關所需電力每月不過一百二十度,為量甚微,而需用則甚迫切。除夜間電燈外,西部科學院及中央工業實驗所均需要電力以供化學分析之用,今若停止供電,其影響所及必甚重大。回憶兩年前各機關感先生及子英先生盛意,欣然遷來北碚,并蒙假惠宇房舍以辦公,復借予地皮使建新屋,時至今日惠宇一帶已形成科學事業中心,外人且有北碚為中國戰時科學中心之說。今者吾人所需之自來水既被大明廠停供于前,必需之少數電力又被停供于后,科學中心勢必將瓦解。先生向來熱心科學事業,自不忍此種現象之發生,況西部科學院為先生所手創,更不忍使其正常工作有停頓之虞。
至大明廠方面所持理由為電力不足,而按之實際則并不如是。查該廠內裝安電燈不下數百,工人宿舍內電燈亦不下數十,均徹夜照耀,輝煌燦爛不關閉,若電力果感不足,何以不節省浪費。近聞該廠與江蘇醫學院定約,自本月份起供給該院制藥用電每月二百余度,而以該廠員工赴該院免費診病為交換條件,此益證該廠電力充裕,乃厚于江蘇醫學院而薄于惠宇各機關,其故殊不解也。至北碚公共電力廠電力甚微,供給北碚市面已感不敷,且近來北碚新興事業甚多,如兼善公寓,如亞洲飯店等,均賴公共電力廠供電,是其供給市面用電已應接不暇,自無余力供給惠宇各機關,而惠宇各機關之用電除仰給予大明染織廠外,別無辦法。
為此敬懇先生設法維持,勸告大明廠主持人繼續供電,則公私感激無涯矣。專此。
敬頌
勛祺!
黃汲清 頓首
五月十八日
對于5月18日黃汲清信中所反映的事情,盧作孚及時作了調查并作建議找盧子英幫助。1940年5月27日盧作孚復黃汲清函:
汲清先生:
五月十八日惠書奉悉。“大明”奉令增加生產,收回廠外供電,以致無法再供惠宇用電,殊為遺憾。科學研究與增加生產極應同時并重,以應抗戰需要。惠宇所需電力已另商北碚區署設法停一部分市場用電,挪以救濟惠宇之各事業,請先生就近洽商子英幫助。至該廠內部用燈,亦應節省,已提起廠中注意。至與江蘇醫學院定約供電一節,據廠中負責人言,系該院少數用電設備供裝廠中,而以優待職工診病為答謝,對該院內部用燈并未供給,等語。特并復聞。
敬祝
健康!
弟 盧作孚
五月廿七日
黃汲清為開展科研工作,曾向時任交通部常務次長盧作孚函索資料,如川滇、滇緬兩路路線圖等,盧作孚皆及時安排搜集,盡力幫助查找,在交通部重慶的案卷表冊中沒有的,又電告昆明敘昆及滇緬兩鐵路工程局代為查找。
1940年2月23日,盧作孚致黃汲清函:
汲清先生:
頃接本部路政司吳紹曾君函稱“昨經濟部地質調查所金耀華君來司交下鈞座介紹函一件,敬悉一是。地質調查所函索之資料,前已著手搜集,唯以需要者甚為廣泛復雜,而本部在渝所有之案卷表冊等項亦不完備,搜集頗感困難,是以迄未完竣,已將此情面告金君,俟搜齊后,當即送達”等語。特此函達,請煩察照。
并頌
時祺!
弟 盧作孚
二月廿三日
1940年10月3日,盧作孚致黃汲清函:
汲清仁兄惠鑒:
頃展九月二十二日手書,敬悉一是。矚寄川滇、滇緬兩路路線圖一節,查該項路線圖部中現無余存,經已電昆明敘昆及滇緬兩鐵路工程局徑行檢寄,希屆時查收為荷。專復。
即頌
公綏!
弟 盧作孚 拜啟
十月三日
2.地質調查所對西部科學院的支持
我國西部幅員廣大,四川及其鄰近地區,如云、貴、陜、甘、西康各省,在西部占有重要地位,而富含礦藏。中國西部科學院地質研究所對于該區域的考察與研究,責任重大,且必須依賴先進的學術機關的指導與援助。
地質調查所對西部科學院多有支持。1930年夏在上海成立中國西部科學院籌備處,實業部地質調查所所長翁文灝與中華職業教育社創辦人黃炎培、南京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中國科學社社長任鴻雋、科學家丁文江、秉志(農三)等都表示大力支持,為籌備中的西部科學院交換標本、介紹人才。地質調查所在西部科學院建立初期及以后亦進行過經濟援助。西部科學院下屬的地質研究所,從1932年成立開始就與地質調查所合作,接受其經濟和技術上的支援。
1930年入地質調查所的常隆慶1932年離所,任西部科學院地質研究所主任。
根據1950年4月22日的中國西部科學院、中國西部博物館人員名冊和同年北碚行政管理處制重慶市人民 *** 原政權人員簡明登記表記載,時任西南地質調查所所長的黃汲清于1949年受聘為中國西部科學院特約研究員。
3.調查科研合作與協作
地質調查所與中國西部科學院的合作,在內遷之前,多是由地質調查所主持、西部科學院派員參與,以四川及其周邊省區為主的西部地區的地質、石油等自然狀況和自然資源調查以及地質圖的編制等科研活動。內遷之后,則由西部科學院發起,邀請地質調查所共同完成。
1931年中國西部科學院地質研究所尚未成立之前,西部科學院即派員同北平地質調查所特派調查員,在四川西部及西康東部調查地質。1931年地質調查所到松潘等地調查地質的是譚錫疇、李春昱。
20世紀30年代,國民 *** 頗注意四川建設,曾幾度派專員來川考察。1935年實業部地質調查所又派人來川調查石油,西部科學院特派地質研究所主任常隆慶(兆麟)一同前往資中、自流井等處,作詳細觀察,每處至少須逗留一兩個月。
在由地質調查所承擔的中國本部地質圖編制工作中,中國西部科學院的科研人員參與其中。成立于1936年、由地質調查所所長翁文灝兼任主任、黃汲清任副主任的中國地質圖編纂委員會,計劃在3年內完成懷寧南昌幅、上海杭縣幅、長安洛陽幅、長沙萬縣幅、桂林湘潭幅、貴陽昆明幅和西寧酒泉幅等7幅1:100萬地質圖幅,并命名29幅以待將來編制。其中的長沙萬縣幅由田奇
、謝家榮、西部科學院一人組成,貴陽昆明幅由黃汲清、譚錫鑄、李春昱、西部科學院1人組成。又計劃從速編制幾個重要區域1:100萬地質圖,其中成都巴縣幅由黃汲清、譚錫鑄、李春昱負責,并加入西部科學院1人。此項計劃由于戰爭的影響延至抗戰勝利后繼續進行。
1939年和1940年,西部科學院理化研究所接受地質調查所委托,進行四川各地的鹽水化驗。
1942年2月,西部科學院地質研究所所長常隆慶等與中央地質調查所李善邦、秦馨菱等,再次探測攀枝花鐵礦。后由常隆慶主筆完成《攀枝花磁鐵礦探測調查》。
中國西部科學院在四川的早期地質調查研究成果,為后來該地區的地質科研工作打下基礎。無疑,文章被引用可以證明其學術價值,地質調查所研究人員的論著中引用到了這些成果。例如,1933年4月中國西部科學院地質研究所印行的常隆慶著,中國西部科學院地質研究所叢刊,之一號《重慶南川間地質志》被地質調查所章鴻釗所著《中國中生代晚期以后地殼運動之動向與動期之檢討并震旦方向之新認識》一文引用,并被王鈺著《關于半河系》參考。常隆慶1937年著《寧屬七縣(現西昌地區)地質礦產》(四川省建設廳出版的四川資源調查報告之一)被地質調查所李春昱的《四川運動及其在中國之分布》一文引用。1933年8月中國西部科學院地質研究所印行的常隆慶、羅正遠著,中國西部科學院地質研究所叢刊,之一卷第二號《四川嘉陵江三峽地質志》被地質調查所王朝鈞、關佐蜀、靳毓貴、李耀曾執筆的《北碚地質志》引用,并被李春昱《雅安期與江北期礫石層之生成》參考。
地質調查所內遷北碚以后,在西部科學院的協作下繼續其科研工作,科研成果豐碩,出版事業不斷。出版品有《地質匯報》、《地質專報》(甲、乙、丙三種)、《中國古生物志》(甲、乙、丙、丁四種)、《中國地質史》、《中國地質圖》、《特刊——中國地層史》、《燃料研究專刊》、《制圖匯刊》、《地球物理專刊》、《地震專報》、《土壤》(分〈土壤季刊?、〈土壤專報?、〈土壤特刊〉甲、乙兩種)以及雜項等共12類19種,非常成系列。1941年只出版了1~3號的《地球物理專刊》,刊載《湖南水口山鉛鋅礦區試用扭秤 *** 探測結果》(李善邦、秦馨菱)、《單極電力剖析》(翁文波)、《霓式地震儀原理計制造經過》(李善邦),記錄了20世紀40年代物理探礦、地震記錄方面的早期成果,為中國地球物理學開創了基業。
據《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所載,地質所在抗戰其間已完成、發表科學論文、報告120篇。其中,《江西南部鎢礦地質志》(徐克勤、丁毅,1943)、《四川鹽礦志》(李悅言,1944)、《甘肅中南部地質志》(葉連俊、關士聰,1944)、《中國主要地質構造單位》(黃汲清,1945,本書是經過長期大量的野外調查之后,總結國內外資料完成的一部中國大地構造的經典著作,使黃汲清成為中國歷史大地構造學無可爭辯的創始人和奠基人)等為開拓性重要調查、研究成果,今天仍具指導意義。
需要指出的是,地質調查所(后1941年被定名為中央地質調查所)在抗戰時期,為了探測抗戰和軍工所需要的礦產資源,在西部科學院的協助與合作下,地質調查所地質與礦產調查工作區域轉向大后方的西南、西北諸省,除找到了上述的攀枝花鐵礦外,還發現了諸如貴州鋁土礦、云南磷礦、廣西鈾礦等一批重要礦產地。為抗戰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4.遷入后的一些活動
1938年1月,實業部改為經濟部,地質調查所改隸經濟部,更名“經濟部地質調查所”。后來,為與河南、湖南、兩廣等省相繼成立的地質調查所區別,1941年夏開始使用“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名稱。
地質調查所有正副所長各一人,分地質調查室、礦物巖石研究室、古生物研究室、地質采礦研究室、測繪室、土壤研究室、化驗室、陳列館、圖書館以及文書、會計、庶務、人事等室[見楊家駱主編《北碚志稿》(二)(1945年)“遷建志”,北碚,1980年油印本]。
1940年秋,中央地質調查所昆明辦事處撤銷,遷至重慶北碚。為防日軍空襲,地質調查所在北碚安置得比較分散。總所設在文星灣現重慶自然博物館北碚陳列館內,圖書館建在2km外的魚塘灣,在遠離鎮子4km的天生橋建造了一些簡易辦公室。
1941年1月5日,中國地質學會在文星灣地質調查所舉行丁文江逝世5周年紀念會,會后楊鐘健作“許氏祿豐龍之采修研裝”的講演,并引導與會者參觀許氏祿豐龍化石骨架。6~8日,許氏祿豐龍在地質調查所對外公開展覽。這是許氏祿豐龍在重慶的首次公開亮相,每天觀眾不下四五百人。1946年,中央地質調查所遷回南京,許氏祿豐龍也被轉運到了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在北京成立,許氏祿豐龍又被轉運到了北京。
1943年,中國西部科學院聯絡中央地質調查所等10余家科研機構在北碚文星灣惠宇籌建中國西部科學博物館(即中國西部博物館)。1944年12月,中國西部博物館在北碚文星灣正式成立。中央地質調查所作為籌備單位之一,負責其地質館的布置。在此期間,亦完成了很多有意義的工作,例如上述的安裝許氏祿豐龍化石骨架活動。此外還有在黃汲清先生的指導下,中國西部博物館的十余名工作人員完成了我國之一件地形浮雕——“中國地形浮雕”,此浮雕至今未作任何改動,足見其科學性,現陳列于館內發揮教育大眾的作用。還有抗戰勝利日益臨近,中國西部博物館將許氏祿豐龍翻制一套模型繼續陳列在展廳內,將正型標本替換下來。
三、內遷西部腹地,意義作用巨大
在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到1937年抗戰爆發前的近10年時間里,中國出現了一個科學文化繁榮時期。而在抗戰時期,全國科研普遍受挫,西部內地卻因禍得福,獨樹一幟。中央地質調查所等科研院所的內遷,是一次“科學內遷”,是地質學等學科研究事業艱苦奮斗、奮發圖強的發展階段。科研機構、科技人員、儀器設備、圖書資料等紛紛轉移至大后方,使戰爭的損失盡量減少,為在大后方繼續科研工作,以及為戰后科研工作的開展,保存了必要的物質條件,民族科學的血脈得到保存。
1.改變了中國地質學等科技的空間分布
科學發展的時空分布受歷史、文化、政治、經濟、自然等等因素影響。抗戰即是一個顯著的因政治原因而改變了近現代中國地質等科技的時空分布的典型案例。抗戰時期,中國的地質等科技格局發生變化,地質等科技中心發生了轉移。重慶、昆明、成都等地成為中國地質科技的戰時主要分布區,而重慶作為戰時中國的陪都, *** 各部門、中央各主要科研機關、重點大專院校等紛紛聚集于此,從而使重慶成為戰時中國科技力量最密集的城市和科技中心。在中央地質調查所遷碚期間,一批中央研究機關因同地質調查所一樣,在中國西部科學院的直接幫助下先后內遷北碚。除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外,分布在中國西部科學院惠宇的其他研究機構有,國立中央研究院動植物研究所(動植物研究所1944年分開,植物所在金剛碑)、中國科學社及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等,與惠宇緊鄰的杜家街分布有國立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經濟部中央工業試驗所等,其他院所如在水井灣的國立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狀元碑的中國地理研究所、后峰巖的經濟部礦冶研究所等,北碚成為當時中國戰時科學中心之說——可謂學術諾亞方舟。抗戰勝利后,雖然大部分科研機關、高等院校回遷原地,但對我國地質學等科學技術的空間分布的影響卻永久地保留了下來,仍然在發揮作用。
2.又一次地質學等科學的本土化過程
盧作孚早年主動走出去、請進來,有意識地推行科學本土化,是一種文化自覺,其最終目標是為當地建設發展服務。抗戰時期,科研機構避禍而來,為適應當時所處環境的變化而把研究對象集中在西部地區,并從純粹理論研究轉向更多地服務于當地的實用研究,自然而然進行科學的本土化。這些科研院所內遷后不但傾力于本職工作,并積極參與到地方經濟文化的建設中,如受北碚管理局委托,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等家單位就參與了編修北碚志的重要工作。
作為國家級的學術研究機構,地質調查所在人才儲備、科研力量、儀器設備、圖書資料等方面在國內堪稱一流。地質調查所到碚研究人員,使內地擁有一批寶貴的高級研究人才。科學家群體在憂思國家民族的命運之時,以一種務實的姿態,堅守書齋,積極作為,除進行本身的研究工作以外,一些還直接加入到當地的研究機關、高校以及工廠等,領銜或參與當地地質等研究工作。例如, *** 20世紀40年代曾在四川地質調查所工作;俞建章1936年回國后任職于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中央大學、重慶大學;侯德封1937~1945年在四川地質調查所工作,后任所長,兼重慶大學地質系教授;楊鐘健曾在重慶大學 *** 任教;李春昱曾 *** 于中央大學和重慶大學,1938年離開地質調查所,出任四川地質調查所所長;黃汲清兼中央大學和重慶大學教授;方俊1943年在中國地理研究所工作;金開英1938年隨同沁園燃料研究室一同轉到重慶動力油料廠。202箱圖書館、陳列館、各辦公室、化學試驗室及土壤室的重要物件運往北碚,充實了基礎設施和研究材料。即使抗戰勝利后回遷原地,但移贈房舍、部分標本等仍然繼續發揮作用。中央地質調查所之一辦公樓(現中國西部科學院舊址內的地質大樓)1946年移交給中國西部博物館。
3.形成西部內地科研文化 ***
盧作孚1930年創辦的中國西部科學院,在開創之初,即為西部內地一面科學的領軍旗幟。后因經費等原因,地質研究所等相繼停辦。然而,盧作孚對科學的熱情并未削減。盧作孚“向來熱心科學事業”(黃汲清),在紛亂的時局里,為知識群體安放下一張安靜的書桌,用中國西部科學院這塊物質平臺,搭建起內遷科研機構的避風港,使內遷機構研究工作的連貫性得到保障,傳承了科學文化的精、氣、神。在國土淪陷的危難之時,中央地質調查所等研究機構,在大后方堅持科研工作,進行“科學救國”。意雖不在改造當地相對落后的科學文化狀況,而實際上先進的科學思維、 *** 、人才、體制等,帶動和提升了西部地區科學文化的進步,出現空前的繁榮。以中央地質調查所為代表的中國大部分頂級科研機構內遷重慶、北碚,地質、生物、農林、工礦、醫藥、地理、物理、心理等形成較為完整的科研體系。內遷給遷入區的科研活動補充了新鮮血液,改善了遷入地區的科研條件,加強了科研力量,改變了科學技術在全國分布不均衡的局面,相對平衡了中國的科技分布。內遷科研機構的學術進程,與盧作孚一直以來在當地所探尋的現代化、科學化的過程相一致,成為抗戰時期以北碚為代表的西部內地近現代科學文化發展的主線,所從事的工作實踐、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使得內地認識自然現象和規律的知識體系變得豐富起來。外來的先進文化繁榮了當地科研文化狀況,呈現出全新的局面,形成西部歷史上不可多得的科研文化 *** 。
四、結語
地質調查所在北碚的時間為1938年7月~1946年1月。經歷了整個八年抗戰時期。期間在中國西部科學院的無私援助和物質保障下,地質調查研究所等各個研究單位的共同努力,地質等科研資源得到了有效整合和充分利用,既改善了地質等科研基礎條件,又促進了區域內科技資源的合理配置和開放共享。全國各科研機構云集大后方,形成內地較為完整的科研體系,地質調查所與其他研究所間更為密切地合作交流,并且與當地社會經濟建設等各個方面的交流合作更為廣泛,在內地形成互為補充、相互結合的科技平臺,改善了中國地質等科學資源分布的格局。內遷院所在原有的科研基礎上,根據戰時需要,調整研究重心于應用科學,注重實地科學調查,獲得大量西部地區之一手資料和標本,充實了該地區的學科研究。內遷給內地提供了強大的智力支撐,帶動了內地地質等學科科研實力的提升,推動了戰時大后方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
參考文獻
[1]蔡元培.中國的中央研究院與科學研究事業.見:蔡元培全集.第八卷[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
[2]黃立人.盧作孚書信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3]程裕淇,陳夢熊.前地質調查所(1916~1950)的歷史回顧——歷史評述與主要貢獻[M].北京:地質出版社,1996
[4]中國地質學會.黃汲清年譜[M].北京:地質出版社,2004
[5]張黎.中國西部科學院理化研究所始末[J].中國科技史料,1995,16(2):33
[6]章鴻釗.中國中生代晚期以后地殼運動之動向與動期之檢討并震旦方向之新認識[J].地質論評,1936,1(1):20
[7]王鈺.關于半河系[J].地質論評,1945,10(1~2):7~8
[8]李春昱.四川運動及其在中國之分布[J].地質論評,1950,15(4~6)合刊:143
[9]李春昱.雅安期與江北期礫石層之生成[J].地質論評,1947,12(1~2):125
[10]趙曉鈴.盧作孚的夢想與實踐[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
[11]陳新,薛運丹.盧氏昆仲與北碚實驗區.重慶文史資料.(第六輯)[C].重慶:重慶出版社,2002
[12]張九辰.地質學與民國社會:中央地質調查所研究[M].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5
[13]張祖林,王永,丁春旭.中國現代科學技術空間分布的形成與發展[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1998,32(1):118~124
[14]孫承烈.北碚聚落志[J].地理,1948,5(3~4)
重慶市自然博物館是什么性質單位
重慶自然博物館是重慶市文化委員會主管重慶自然博物館歐陽輝職稱的市屬文化事業單位

![[重慶市]重慶自然博物館歐陽輝職稱,重慶自然博物館館長歐陽輝](/zb_users/upload/editor/water/2022-12-15/639b37e1c5bd5.jpeg)



 獲取資料
獲取資料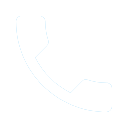 顧問電話
顧問電話
評論已關閉!